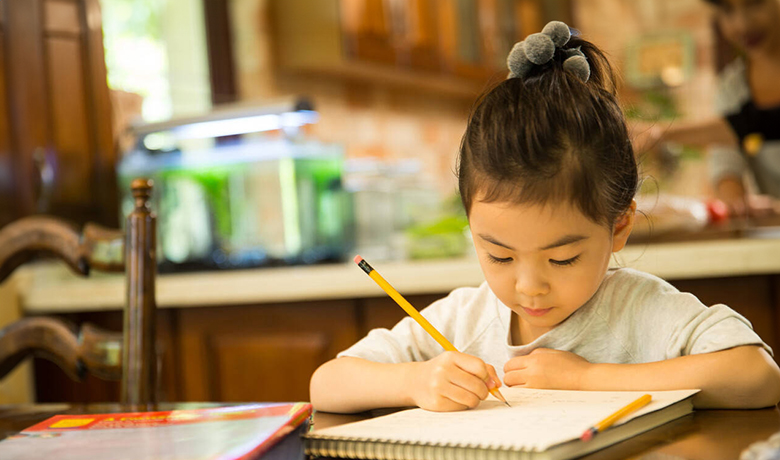吴爱华
我多年未回老屋了。其实,我离它不远,我居住的城市距离它大概35分钟的车程;从哥哥家回去,只需步行10分钟。这么多年来,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,常常会想到它。然而,一次又一次地行至回去的路口时,我却又停下脚步,遥望着它的方向。每每这个时候,在我的心里,似乎有两个自己在打拉锯战,一个想回去,另一个却说,算了,还是不回去了。最后,总是后者胜利。这种复杂的情感,曾经让我感到无比困惑。
老屋叫白楼厦,最昌盛的时候,住着二十多户人家,一百多号人。除了娶进来的媳妇外,其余的人身上都流着相同的血液。楼里的男女老少,不管血缘亲疏,一般都是按辈分称呼的。小辈见到长辈,往往会很高兴地先叫对方,长辈则会满心欢喜地拖长“诶”的尾音,答应小辈。然后,满脸慈爱地叫一声小辈的乳名,并问,你吃饭没?或是你要去哪里玩耍了?
记得小时候,大人收完晾晒的谷子后,偌大的晒谷坪便是我们撒欢的乐园。我们可以尽情地奔跑,还可以捉迷藏、跳绳、踢毯子等等,大家玩得不亦乐乎。稍大懂事点的孩子,差不多玩到饭点的时候,自己会回家。小点的孩子,往往玩个尽兴,听到父母亲或是哥哥姐姐一边喊着自己的乳名,一边拉长尾音喊吃饭啦吃饭啦的时候,才各自回家。每到假期,整个老屋仿佛是孩子们的战场,大家在房前屋后你追我赶,玩打仗的游戏。
父亲退休后,带着母亲回到老屋住了几年时间。在这期间,我时不时地会回去看他们。后来,哥哥嫂嫂劝说父母亲搬去和他们一起住后,我回老屋的次数就少之又少了。只是,偶尔会回去看看独居的三婶婶。再后来,三婶婶去世了,我就更难得回去了。几年前,我和大侄女从哥哥家徒步回老屋,走到半路,一条宽广的双向三车道带双辅道的大马路横在我们面前,我们极目远眺,努力地在寻找回老屋的路。正当我们感叹环境变化之大,连路都找不到时,对面突然驶出一辆摩托车来,我和侄女同时兴奋地说道,是四妹。四妹是我的堂嫂子,她一家原来也住在老屋,多年以前,搬迁出去了。她见到我们,骑车到我们跟前停下,我们亲热地聊了几分钟的家常。道别后,我们向她突然冒出来的地方横穿马路过去,找到了回老屋的路——原来的村道。
由于搬迁的原因,老屋早已人去楼空,到处杂草丛生。有的草齐人腰,坍塌的土堆上,甚至长出高大的树来,让人感觉无比的荒凉。它标志性的建筑——五层高的白楼,外墙脱落严重。这座300多岁的老楼,离开了人气的滋养,终究敌不过风雨的侵蚀,我似乎看到了它倒塌的那一天,内心不禁一阵怅然若失。这次之后,我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记忆中,老屋人气旺盛,特别是春节,更是热闹非凡。外出的人,不管有没有赚到钱,再远也要归家的。春节期间的每个晚上,老屋锣鼓喧天,有舞狮和拳术表演。大年初二是绝大多数人回娘家的日子。这天,姑姑和姑爷是大家共同的亲戚。那个时候,大伙大多喝自酿的米酒,用吃饭的小碗来喝,一斟就是满碗。
今年正月初六,我们从四面八方奔回老家祭祖。当我们齐聚爷爷奶奶坟前的时候,我却发现我们大家似乎成了最陌生的熟悉人。我们之间,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过多的语言交流,走完祭祀流程后,就各自散去。是不是我们一大家族的人住得太散了,平时难得见上一次?抑或是大家平时疏于联系,以至于见面时,大家一时不知道要聊些什么?在我的记忆里,小时候,我是非常喜欢跟随大人去祭祖的。我们小孩子一路上连蹦带跳,大人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,从老屋一直说到爷爷奶奶的坟前。回程亦是如此。一想到这些,我就特别怀念老屋,特别怀念大伙儿在老屋的日子。那时候,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轻松的,和谐的。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,吃饭都是可以端着饭碗,走东家串西家的。这种群居的生活,无形中,培养出了大家的“自家人”的意识。去到外地,遇到族人都会倍感亲切,因为是屋下人(自家人)啊。
近段时间,我一遍又一遍地回想起以上的一幕幕,心中的那个困惑,终于被我自己解开。我之所以想回去,是因为那里承载了我太多的童年欢乐;我之所以不想回去,是因为那里没有了我的父母亲,没有了我所牵挂的人;我之所以怕回去,是因为我见不得它的破败与荒凉。
渐行渐远的老屋啊,小时候,我住在你的身躯里,现在,你深深地驻扎在我的心里,直到永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