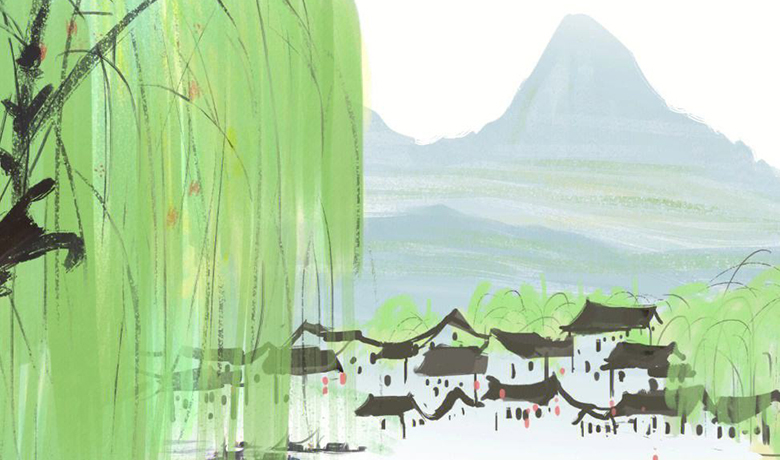
当清明是节气,草长莺飞、花红柳绿,最是踏青游春时,呼亲唤友、纸鸢青粿、赏花煮酒,流连于春光轻松愉悦。当清明是节日,春雨含冬、芳草萋萋,最是慎终追远日,祭祀扫墓、焚香祭拜、寄托哀思,沉浸在过往肃穆庄重。
扫墓是清明节重要的活动,不可或缺。随着城市化进程,市郊的很多山头改造成了公园,很多墓地也随迁进了陵园,扫墓仪式简单了许多,而小时候的扫墓不是这样。
记得以前每年清明都要和家人长辈去扫墓,墓地位于城郊一座小山上,坐着车沿着乡间小路来到位于山脚的亲戚家中,几家亲戚会合后,拿上扫墓的各种物品,沿着泥泞小径蜿蜒上山,边走边用枝条打着两旁杂草,正所谓“打草惊蛇”,同时用镰刀劈除挡路的杂草荆棘。山路旁野草茂密,各式野花开得正盛,蝴蝶、蜜蜂翩翩起舞,都是春的气息。
除此之外,路两旁错落着层层叠叠风格和年代各异的坟墓,小时候并不害怕只觉得好玩且好奇,常常故意凑到墓碑前去认读上面的碑文。每到这时,母亲总会紧张异常,抢前一步把我拉开,嘴里念念有词地说着百无禁忌、神鬼勿怪一类的话语,但是等她略微放松了警惕,我立刻又会找机会偷偷去瞄路边墓碑上的文字。其实碑上的文字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,内容千篇一律,大概写的都是墓主和立碑人的身份、姓名和年代等等,但是对于懵懂好奇的小孩来说,这些墓碑如同陌生人递来的名片,非但不阴森恐怖,反而充满着一种让人一探究竟的吸引力。当然这上面没有联系方式,也没有邮箱地址,或许以后等我们这代人故去时,可以加上生前使用的微信号,把朋友圈开放给前来祭拜的人品读,倒也未尝不可。
清明若是天气晴朗,近午的太阳常是火辣的。当我们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地到达本家的墓地,登高远眺,春风拂面,贪婪地呼吸着清新空气,疲劳感顿消。大人们稍作休息,撸起袖子便开始干活,男人们拿出锄头、铁锨、镰刀等工具,绕着坟地一周把杂草除去,女人们拿着扫把将泥土、杂草扫开。平时难得一见的亲戚们见了面分外亲切,边干活边拉起了家常:爷爷奶奶在世的故事,儿子上大学,女儿找对象,市场的物价越来越高,谁家又买了新房等等,大家说着、笑着,其乐融融。小孩子们刚开始还老老实实地帮大人们打下手,但天性使然,被锄头镰刀惊起的硕大虫蚁、五颜六色的野花野果子,各种新奇生动的事物让孩子们将一切抛到脑后,极快地融入春日的嬉戏中,像小鹿似的嘻嘻哈哈、打打闹闹、跑跑跳跳……肃穆的扫墓成了欢乐的春游,不过,这生者和睦相处的天伦美景,不就是祭奠亡者的最好心意吗?
扫墓结束后,大人们总是会在墓边一棵枣树的枝丫上挂上长长的一串鞭炮点燃。枣树是早年种下的,寓意家族后人多子多福,已然从不到两米高的树苗长成了两层楼高、一人环抱的大树。孩子们对这棵树很有感情,总是担心它被炸疼炸伤,事后总要上前心疼地摸摸树皮,偷偷地打开几瓶矿泉水浇在树底,最后再插上三根香,表示小小的感谢和安慰。其实,大人们都看在眼里,也不来阻止孩子们的自发行为,大概觉得这是一种善念值得鼓励吧。现在回头想想,这些细节中蕴含着的朴素的中国式家庭教育,不需要什么费力的道德说教,也不用太多的辞藻来修辞,潜移默化地种进了一干后辈的心田中,成为将来为人处世的准则。
扫完墓,大家会带着一些枝条、青草回家,意为“压青”辟邪。此时我们总爱循着另外一条路下山,这条路比上山的路要远一点,但好处是可以看到黄灿灿的油菜花地和绿油油的麦田,并在田里挖一种叫“薤白”(“薤”读作“谢”)的野葱,俗称麦葱。薤白叶片是细长、中空的,兼具葱、蒜、韭菜的特点,山野常见,是老家人春天经常食用的野菜。小孩们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,依旧是采挖薤白的主力军,最后采挖总会演变成一场小小的比赛,看谁采得最多。
回到亲戚家里,大家都已是饥肠辘辘,幸好早有家人端出热腾腾、香喷喷的菠菠粿,并把那些刚摘下还带着泥土的薤白洗切,直接加入鸡蛋、虾米、海蛎、地瓜粉等,下锅煎成饼,简单的食材,天然的香味,疲惫的身体仿佛被瞬间激活,这个节过得有滋有味。
清明节是以节气兼节日的民俗大节,作为祖先崇拜这一中国人特有的民间信仰现象的表现方式。在这个节点,千百年来家族团聚、慎终追远,一起祭拜共同的祖先,重复着同样虔诚的礼仪,烧化出同样悠扬的青烟,品尝着同样可口的美食,并且我们的孩子们还将继续坚持把这些事做下去,每当想起这些,心里总有种沉甸甸的踏实感。中国人对祖先的情感主要体现在春节、清明等几个重大节日上,虽然很多传统仪式被人们忘记了,但回家过年、回家祭祖、认祖归宗,体现了中国人文化认同和血缘亲情,对祖先敬畏产生的道德约束和情感寄托,这就是中国的清明节兼容并蓄、和谐统一的价值所在。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