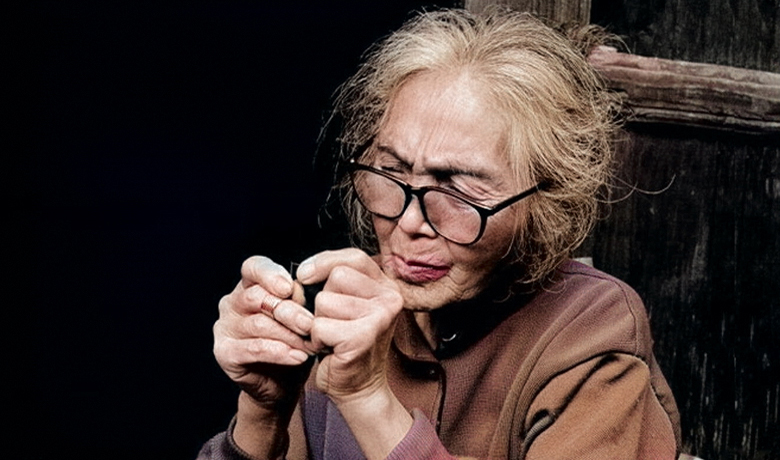青色
故乡二鹰山上的芫花,总让我魂牵梦萦。它有着丁香花的容颜,也有着崖柏的坚韧。
二鹰山是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一座小山,位于平潭岛中部,靠海但望不到海。山上生长着无数的花草,它们有着朴素的力量,迸发着野花野草固有的幽微勇气,是这座山最为生动的部分。这些野花野草也构成了童年那个懵懂少女的粉色世界。
童年里,芫花遍布田埂及山坡。每至春天,我的家乡便被这种蓝紫小花包围,但后来渐渐消失了。经年后,我忆起它依然心生悸动。它像一团烈火,灼着我的少女梦。这是离人的乡愁!无言叹白首,犹寻少年花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2019年我终于又在故乡找到了它。
自从得知二鹰山上有芫花后,身边的伙伴就惦记上了它,其中一位是从事中医药学研究的老杨。虽说芫花在福建境内多有分布,但呈现在植物学家面前的往往是它的“族人”——了哥王。去年,我们就曾驻足这里,可惜花期已过,只能在山巅惋叹。不过,细心的老杨在繁密叶底发现了它的果——豆大的白果,如粒粒珍珠,掩映在碧叶之下。我惊讶于它的存在,汗颜于自己的粗心。
今年我恐再错过花期,时刻警惕着。雨水后数日,“掐指一算”,它该开了。请了平潭当地“花探”去二鹰山探寻。果不其然,消息传来:芫花已盛开!当机立断,约上老杨他们一起奔赴平潭。朋友欣桐在电话那端一再嘱咐:“风大,一定要多穿些!”次日,一行十多人的队伍出发了。
这两年因追花,我们多次来到这个偏僻小村,登上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山坡。村民们对于我们的到来已见怪不怪。自从附近建了动车站,铁路穿二鹰山而过,村人大多搬迁,本就不大的村庄只剩十余户的村民留守。小村野草蔓生,藤蔓纷披,却因此留住不少原生珍稀植物,包括去年我们植物考察时发现的濒危野大豆之一的烟豆。
当我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,芫花的芬芳已飘荡在空气里。二鹰山因我们的到来而变得热闹。迎着九级猎猎寒风,如紫丁香般的芫花就盛放在山坡上、石缝中,风恶作剧般拼命地摇晃它,未真正见识平潭风的小伙伴,总算领教了一次它的狂野。与风同样疯狂的还有我们。头发失去理智地在脸上甩打,人差点被卷走,但我们依然在花前手舞足蹈。芫花如一个古老的谜题,让所有人迷醉。
在风中上下翻腾的芫花,有阳光洗濯后的轻盈与通透,又有风雨倾轧后的从容与沉着。它并不高大,却让自己的每一枝都盛满鲜花和故事,读来令人怦然。它像极了那个惆怅的“丁香姑娘”,便有了“野丁香”之别名。在向北的山坡上,它锦绣般铺满山野。我骄傲地告诉老杨,童年的我便是在这样开满芫花的野地中长大。
蚀骨的寒风把我拖回记忆盒。少时的我爱种花,常把山花移至家,唯芫花从未成活。所有野花中,芫花最难采。它长不盈尺,却出人意料的强韧。强折枝条是折不断的,只能在枝腋处,顺着分枝的逆方向,方可撕扯下来。外表柔弱的它,何等坚执!时光回溯中,我猛然醒悟,在贫瘠土地里,在风的淫威下,唯有长成坚不可摧的自己,方能遇见未来,方能抵御岁月无情。一百多年前,英国植物猎人威尔逊来到中国西部,被芫花惊艳。它成片地匍匐于脚下。他发誓要将它们带回欧洲,并预言这种美丽的花儿将在世界各地的花园大放异彩。遗憾的是,芫花令他失望了。异国他乡的“锦衣玉食”勉强喂活了它,它却不愿露出谄媚的笑容,渐渐枯萎。不是每一种美丽的花都喜欢被圈养,它可以卑微,却不能失去风骨。直到现在,我们仍极少在花园里见到它的踪影,但它却穿过时间的迷雾和挣扎,重回我的面前。
或许,芫花很轻,轻得如一片飘浮在空中的羽毛,入不了旁人的心。但对于我来说,它是故乡花,重如搁浅的岁月之船,刀削斧凿般永刻我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