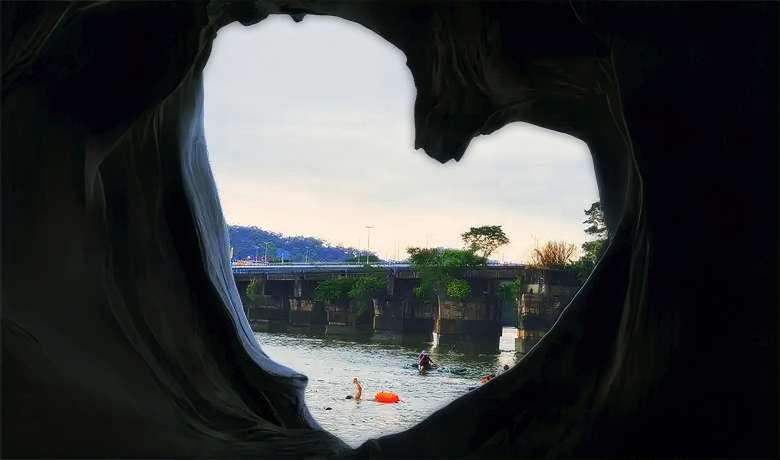黄鹤权
小时候总嫌奶奶灶台前的煤烟呛人,可现在闻到巷子口烤红薯的焦香,突然想起她用土灶焖了一下午的芋头。那带着粗粝感的甜糯,就是后来翻遍菜单也找不回的“古早味”。我记得,当时掀开锅盖,蒸腾的热气裹着芋香漫过鼻尖,奶奶总爱用布满老茧的手,轻轻刮去芋头皮上烤焦的纹路,露出里头金灿灿的绵密,一口咬下去,喉咙被熨得发烫。
这就是我认知里的第一口古早味。其实,这词儿本是闽南人挂在嘴边的念叨,说的是海蛎饼在油锅里冒泡的酥脆,是石花膏熬足四小时才有的清冽。随着城市化的脚步加快,消费主义浪潮悄然涌进街巷。当霓虹灯取代了巷口的煤炉,当标准化生产线上的糕点被贴上“怀旧”的标签,不知从何时起,街头突然冒出许多打着“古早味”旗号的店,卖着包装精致的“怀旧面包”,玻璃柜里的糕点闪着工业糖精的光。
上周经过一家新开的甜品铺,橱窗里的凤梨酥印着复古花纹,咬开却只剩齁甜的馅料,连一丝凤梨纤维的颗粒感都尝不出。有人说这是跟风,可我总觉得,大家追的不是那口味道,而是藏在味道里的“老日子”——像外婆在纳鞋底时哼的小调,像老收音机里沙沙作响的戏曲,明知不完美,却舍不得丢。
就像我老家巷子里的王大爷,守着个铁皮爆米花机三十年。每次转炉“嘭”地一响,方圆百米的孩子都捂着耳朵尖叫着冲过去。他总戴着顶洗得发白的鸭舌帽,布满裂口的手攥着摇把,铁锅里玉米粒翻滚的声音,和着煤炉噼啪的爆裂声,成了整条街最热闹的乐章。爆出来的玉米花带着柴火味,不像超市里袋装的那么甜,却总能让蹲在一旁的李奶奶红了眼眶。她说这味儿让她想起年轻时,丈夫用省下的粮票换爆米花哄她开心的光景。那时电影院门口的爆米花摊前,总排着穿蓝布衫的小情侣,捧着热乎乎的纸袋,连碎屑都舍不得抖落。
据我观察,现在的人总说“快节奏”,可偏偏对“慢”出来的东西上了心。比如,我家邻居王姨每年夏天都要晒梅子酱,摘果子、洗晾、熬煮,折腾整整三天。梅树是她和老伴在年轻时亲手栽的,结出的果子酸涩中带着回甘。她把梅子在竹匾里摊开,让阳光一寸寸渗进果肉,熬酱时守在灶台前,用木勺慢慢搅动,香气飘满整个楼道。她说自己做的梅子酱,能尝出梅树在太阳下晒了多久,尝出春风拂过枝头的温柔。
还有些古早味正在消失。前阵子回乡下,发现小时候常去的豆腐坊关了门。褪色的木招牌还挂在墙上,“手工豆腐”四个字被雨水泡得模糊。老板的儿子说,做手工豆腐太累,不如去城里打工。这让我一时无言以对。是啊,他说的有道理。但可惜了,可惜的是——从前每天清晨,总能听见石磨转动的吱呀声,还有豆浆煮沸时泛起的奶白泡沫,如今都被轰鸣的机器声碾碎。
我对老板儿子说起了泉州一家百年卤料摊。那里的一家人起早贪黑守着老方子,八角桂皮的香气钻进青石板缝里。顾客愿意驱车半小时来吃,就为了那口浸透时光的咸香,连汤汁都要打包回家煮面。我对老板儿子说,哪天豆腐坊重开记得喊我。
那天,我到一家咖啡店,看到菜单上写着“古早味拿铁”,撒着可可粉的奶泡上摆了块迷你鸡蛋糕。我没点,转身去了巷尾的老面店。铁皮卷帘门哐当拉起,蒸笼揭开的瞬间,白雾裹挟着麦香扑面而来。老板正把刚出炉的馒头往竹筐里放,掌心的温度让面团多了几分暖意。
咬下一口馒头,松软里带着嚼劲,没什么特别的调味,却突然明白:古早味哪有固定的样子?它是奶奶刮芋头时指甲缝里的焦痕,是王大爷鸭舌帽下被煤烟熏黄的鬓角,是邻居阿姨竹匾里晒了三天的梅子……是那些被我们藏在记忆深处,一想起就暖烘烘的“旧时光”啊!
或许某天,当街角的面包房飘出新鲜出炉的麦香,当偶然听见老式爆米花机的声响,那些关于“古早味”的回忆,又会像潮水般漫上心头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