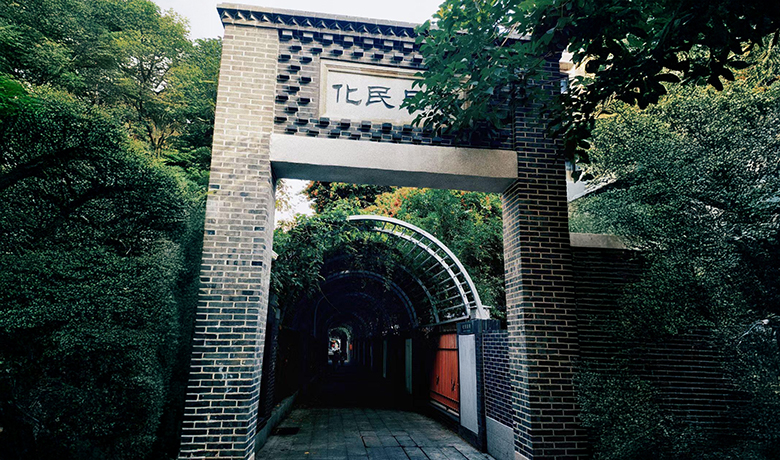姚俊忠
小镇在闽北的山城中。镇的尽头有个水碓,我们叫它“碓下”,是小镇街尾人舂米、榨菜籽油的磨坊。对于童年的我来说,这里是个神奇之地。
水碓有两棵参天大樟树,粗壮的树枝被厚厚的微微翘起的树皮包裹着,弯弯曲曲向四周延伸,浓密的枝叶像一把巨大的遮阳伞,把整个水碓笼罩在怀里。水碓的水车在吱呀吱呀地转,石臼里堆着稻谷,通过转动的木轴连接着水车的木碓,一上一下地磕碰着,稻谷便在石臼里脱了壳,露出或暗红或雪白的米粒。
几个光着膀子的大汉,喊着号子,来回摆动着一根长长的粗大的原木。原木用铮亮的铁圈箍紧,来回撞击楔子,楔子同样用铮亮的铁圈箍着。随着阵阵清脆而沉闷的撞击声,油槽里的“油饼”便流出一缕缕菜油,顺着木槽滴入油盆中。顷刻间,作坊里油香四溢。
穿过碓下,就来到清澈见底的小河。河水浅浅的,只有五岁孩子齐胸深浅。现在想来,那根本不是河,只是一条小沟,是引河水来推动水车的河沟。小河沟是用一块一块鹅卵石砌起来的,大小不一的鹅卵石,经河水常年冲刷,磨去了棱角,块块都圆润光滑。清澈见底的河水在鹅卵石中流淌,柔顺、欢快、清凉。对岸的石缝里长满了水草,蜻蜓张着翅膀在草间飞舞。蹚过齐腰深的水,慢慢靠近,伸出拇指和食指,悄悄去捏蜻蜓竖起的翅膀。蜻蜓精灵得很,在手指捏住的一瞬间,振动翅膀从指缝中溜走。
河里的小鱼一点也不怕人,一群一群地围着我们的腿转,伸手去抓,则都溜走了,连鱼尾都摸不着。玩伴郝明跟我同年,个还没我高,但胆子比我大。我们一起把洗澡的毛巾摊开,一人抓一头,弓着腰从水下捞,眼看着一毛巾的鱼,出水时却一条都没了。偶尔也有一两条来不及逃离,躺在毛巾上跳跃,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。
郝明也会带着鱼竿,挖上几条蚯蚓,拉着我到大河里钓鱼。我在河滩挖沙,偶尔挖出一窝小小的蛋,他说是蛇蛋,吓得我赶忙埋回去。郝明拔一根韧性强的草,在一头打上结,把钓上来的鱼从鱼鳃穿过,一条接一条穿起来,小半天,他就能钓一大串鱼。
童年的日子一晃就过去了,我随父母到省城上学。三十年后,我回小镇,正遇到郝明。他蹲在老屋门口,叼着烟,胡子拉碴,看上去像老头,差点没认出来。我很高兴,迎上前打招呼,可他蹲在原地,一动不动,只是哼了声,算是应了我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我这么冷淡,也没敢多问,寒暄几句,就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