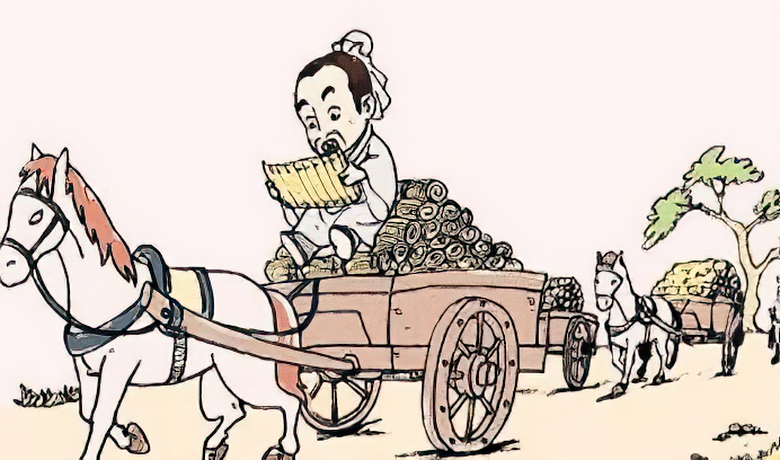在福州,没有一种料理过程比炖罐更不动声色。把盛满食材的罐子,装进热气腾腾的蒸笼里,剩下的步骤,交给高温和时间打理。蒸笼里的水蒸气打着褶儿,缠绕在炖罐四周,逐渐舒展出浓郁而滚烫的香气。高温让食材肉质紧缩,溢出的动物脂肪化作细密的油花,汤色渐沉,却依然清澈见底。
老福州的炖罐,有着自己的脾气:食材绵软,汤头清冽,没有过多的调味,每日限量供应,悄悄地售罄。土鸡、土鸭、羊肉、海蛏、牛排、大猪腰……万物皆可煲。在寒冷的冬天,喝下这一罐鲜美醇厚,就足以抵御这乍暖还寒的冬天了。
饭点未到,这家榕城老字号的店里已被坐满。炖罐在蒸笼中码得齐整,清甜的香气涌进鼻腔里。目鱼、猪肚、排骨、虾仁炖蛋、小佛跳墙……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,样样皆可作为招牌。
小炒们荤香油亮,冒着淡淡虾油味,被分类码好,待人挑选。在这里,食客们惦记的,除了炖罐,还有蟳饭。把橙红的蟳和调味过的糯米同蒸,吸饱了鲜香的糯米颗粒饱满,勾得人馋虫四起,胃口大开。
在这里觅食,从点菜到吃饱得一气呵成。“请问在哪里买单?”总有初来乍到的食客这样问。“先食”,店家的回复短促有力。
在福州炖罐圈,古街老牌炖罐的江湖地位,可往前追溯三十余年。三十多年来的每一个清晨,不少人还在和被窝纠缠,小店的灶台早已醒来,开始一段从清晨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四点的营生。各种新鲜的食材得先被处理干净,然后才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。
把食材分类码进炖罐里后,盖上蒸笼,在滚烫的蒸汽里待上一阵儿,就能成就一盅好汤。踏进店里,总会有亲切的福州话迎面招呼上来:
“依弟,食饭还是食面?”
“食饭吧。”
一碗木鱼筒骨连同米饭一起被端上桌,肉和汤界限分明。扒一口米饭,喝一口汤,就能感受到香气四溢的绵长滋味在齿间流窜。软糯的炒白果,吸饱了配菜的鲜甜,化作一抹油亮亮滚进舌尖,最后,总会拉扯着馋虫吞进胃里。搭一份虾油味十足的拌空心菜,咸鲜和脆嫩填满口腔,一餐才算完成。
在桂香街,当一家老炖罐店又开始新的一天的营生,时间已经不知过去了多少年。这里出售的炖罐,价格在11至20元不等,每一个炖盅都塞满了新鲜食材,有的甚至快要溢出来。热火朝天的生意量,从红底黄字的菜单上就能看出来。售罄的炖罐,贴着了色彩不一的磁贴,看起来怪可爱的。饭点还未过,我们心心念念的鸭腿罐和海蛏罐就已经卖完。
我们点了一份鲜嫩的土鸭罐,汤头清甜,没有过多调味,肉质十分软烂。整块含进嘴里稍稍用力,趁牙齿不注意,骨头就从肉的缝隙间溜了出去。蛋炒饭粒粒分开,缝隙被蛋填满,盛在不锈钢碗里,看起来黄灿灿的,每一口都沾满福建老酒的滋味。
施浦后路上的邵武拌粉,摊主的个性比美食还要加分。毕竟,作为一家拌粉店,它竟然跻身“炖罐江湖”。这里的炖罐分量十足,罐子里养着一汪清白鲜美,即使店门口的灶台上悬着“猪巨贵”。喝一口汤,就能感受到“巨贵的”香气的在齿间流窜,滋味绵长。
店主是一名退伍军人,07年时开始摆摊卖炖罐,生意好的时候,常奔跑着穿梭于食客间,于是便有了“唐跑跑”的称号。2013年,他搬到了现在的店面,炖罐的种类也渐渐丰富起来,多达四十余种。这里出售的炖罐,都藏着排骨二三块,骨肉间的胶质让汤头更加醇厚鲜香。
竹荪猪脑炖罐,汤头很清,不带一丝浑浊。猪脑被处理得很干净,用勺子轻松舀起,软绵绵地躺着,轻轻一抿,就化在舌尖。牛骨髓外皮坚韧,和牙齿做抵抗,发出清脆的咯吱声。内里柔软,吸饱了汤里浓浓的老酒味,在咀嚼间就销声匿迹,只留鲜甜在喉头。
咸香四溢的猪油拌面,从面到调料,都是来自店主的闽侯老家。面条又细又长,挂满了葱油酱汁,囫囵几口,便可吸溜干净。
在福州,老话说:“爱喝汤的人有情。”毕竟,愿意等待这样漫长且耗时的料理,少不了得有点耐心,才守得住这一罐子绵长鲜香。而在这一罐不动声色里,时间凝结的智慧渐渐化作温热的人情味,填满匆忙的生活琐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