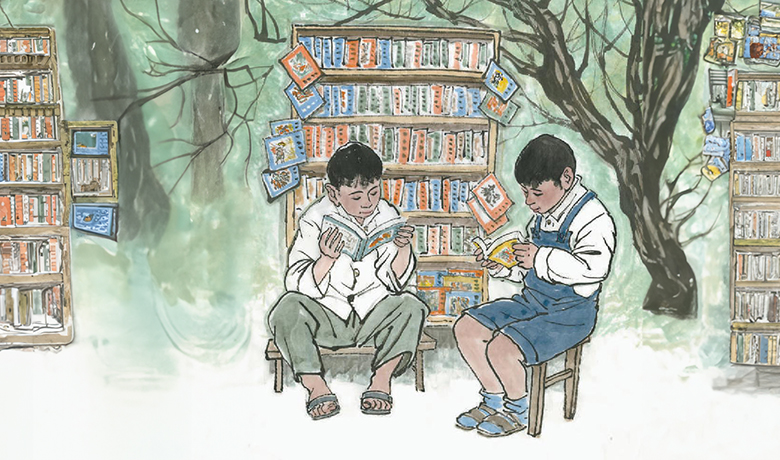陈其彬
我对板车的认识,缘于跟父亲拉板车开始。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父亲承包大队碗厂三年拉碗合同。为此,父亲花费三十五元钱,去街上购买板车轮。随后,父亲上山砍伐几根杉木,锯开晒干,自己动手制作板车架。
大队碗厂在后山一座山坡上,一般每月烧一次窑,出一窑碗,拉一窑碗。一条山路,弯弯曲曲从山坡蜿蜒至大队村部仓库,有近二公里路程。每拉一趟车,要爬坡过坎二三道。时值夏季,我小学毕业后,碰上“文革”,中学停招。我只好接替母亲跟着父亲去推板车。说是推车,其实包含当搬运工,因为碗具都是拉推车人员负责装卸车。
第一天上班,父亲前面拉车,我跟在板车后面助力,车在平路我推车走,板车下坡,我一只脚踩上车尾“木托”,车速慢慢下坡。这时“木托”着地与路面摩擦,一路上发出吱吱喳喳响声。“木托”是用一根松木做成,直径十三四厘米。它是拴在板车架底部中间,尾部比板车后架多出三四十厘米,主要便于推车人在后面用脚踩刹车,控制车速。
下了这道坡,板车过了一个坎,又要再爬上一段长坡。父亲的肩膀背上车把拉绳,双脚蹭地,弯着腰向前拉着麻绳一步一步住上爬。我则在后面,两手摁住两边车架后部立柱,使劲向上推车。一会儿工夫,板车爬上坡顶,我们都松了一口气,接下来又走过一段平路,板车到达仓库。两人忙着卸货入库。来回一趟,需要一个多小时,一天拉七趟,耗时九个多小时。
几天后,窑坪出碗窑层越出越高,来回一趟搬运的时间也增长。这时,父亲为提高工效,用一担畚箕挑碗,每挑四筒。我因人小挑不上,每次再用双手抱着一筒碗具下坡。但两只脚好像不听使唤,不停地颤抖着。父亲见状,叫我先站住双脚,然后一只脚一只脚往下走,走一步,稳一步,步步着实。照着父亲的说法,脚步稳定了很多,不过初次抱碗下坡仍有些不习惯,只好走走停停,拖泥带水,一车只抱了几筒碗。
有一天早上,一场蒙蒙细雨,让窑坪小路变得湿滑。我下坡路时,噗噗一声,连人带碗不慎摔倒在地,屁股着地,痛得直叫。父亲看见,立即上前把我扶起,用手拍拍后面裤子的土,说:“小孩摔倒没关系,摔一次长一寸。”我一听也笑出声音。
跌倒,爬起!再跌倒,再爬起!久而久之,抱碗下坡,我再也没有摔倒了。
拉板车最怕运输过程中,板车轮胎发生泄气和爆胎。轻则泄气,可以用两根相应的顶棍撑住两边车把,让套勾里轮胎轴松动,再用风筒打气,倒是很快解决问题。如遇爆胎,麻烦多些,先要卸下车货,再把轮胎拿出,送到附近的摊点修补,费时又费劲。更为难堪的是,拉板车中途下雨,道路泥泞,人的脚如同穿上一层厚厚的海绵鞋,两只轮胎沾满泥巴,动弹不得。只好停下板车,用一根竹片慢慢刮去轮胎上的泥巴,才可以走动。可是还没走多久,轮胎又沾满泥巴。这时,复又停车刮泥巴。走一段,刮一段。
第三年春天,我向父亲要求学拉车,当个车把头。
回想起第一次当车把头时,也是先走平路再下坡路。但下坡不是很陡,我在前面拉车,父亲在后面一脚踩着“木托”,车速并不是很快,但是我掌控的车把头,却晃来晃去。好不容易拉到平路后,父亲说我,“像这样掌车把头很危险,不一定什么时候晃到人。”他当场站在车把头中间示范着:“拉车眼睛正视前方,双手摁住两边车把,人走中间,稳定迈步,车把头不会摇晃。”果然,我再拉车时,车把头就不会那么晃动了。
“上坡要拉车,下坡要掌车,平路要走车。”父亲的三句拉车口诀,是他多年的经验积累,言简意赅,点出了拉车的要点。比如板车下坡路,要怎样控制车速,什么路面需要快车,什么坡段可以放车,要想掌握这些要点,也并非一朝一夕,需要我在一车车操作中具体尝试,在一次次探索中总结运用。
不到半年,我就掌握了拉车的技术要点,当起车把头来,轻松又省力。父亲看在眼中,喜在心里,认为家里拉板车有接班人了。
春暖花开,万物生发,家里好事一茬接着一茬来!年初,父亲被选上大队干部,同时碗厂三年拉碗合同到期,身材瘦小的父亲也不用再干这种重活了。随后,中小学复课招生,我有幸成为县里“文革”后的首批中学生。此后,我和父亲不再专业拉板车。但这部板车也没闲着,农耕时节,我和父亲会利用空余时间,为生产队拉稻谷、甘薯、油茶,运公粮、肥料。平时不用时,父亲和我总把车轮擦洗干净,锁进柴火间,板车架则放在后院干燥遮阳的地方,以防雨淋受损。
从少年到青年,我拉了九年板车。或许,当时这份重活并不适合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,但是,我并不后悔,而且时常怀念这段时光。因为,在我开始形成世界观的少年时代,它让我懂得了用劳动去创造生活,用今天的话来说,“幸福是奋斗出来的”。这让我一生受益良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