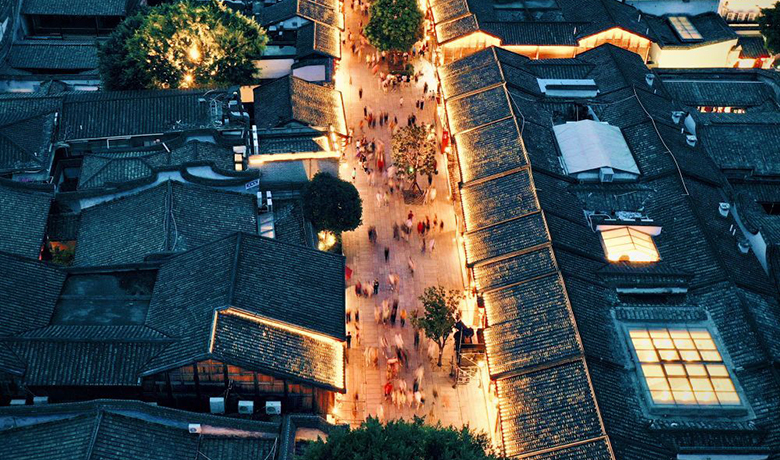吴晟
四百年后,我来了,穿过缓缓江流攘攘街声,停车。在小孤山旁,石阶斜斜向上伸,伸入青青如苔的历史。山门前的石壁上,攀爬的榕根纵横交错,繁密如二维码,目光一扫,隐约可见它的前世今生。
那时,先有桥,在福清南门外,始建于宋朝的桥,却直直通向明朝的县衙,为堪舆所忌,时人皆谓应移建他处。当地学者叶朝荣为此周旋而未果,就连他的儿子,内阁首辅叶向高,也忧于经费人力,不敢贸然动工。后来,叶相之子叶成学着手募集善款,率父老向县令凌汉翀建言获准。县令也捐出自己的俸禄,遂动工移桥,并改木为石,修成龙江上游第一桥,故名龙首桥。此后,每逢元宵佳节,众乡亲皆盛装过桥以示吉利,尤其新婚夫妇,喜欢携手过桥,同心祈福,风尚渐成习俗。“利桥”美名,遐迩流传。
与修桥同年,即1606年,为“补龙江地势之旷”,“点缀融城风景之不足”,需建塔以代文峰。于是,一个班子,两个项目,十载工期,史料还记录了一个名字,名匠李邦达,由他负责设计与施工。建塔所需的优质花岗岩,采自龙江入海口的石山,以船运输,潮起潮落,帆去石回。塔身要那么高,石材是那么重,且层层递进节节高升,直到登峰造极,这都怎么做到的?他们的办法是垒土成坡,每造一层塔身,就垒高周边地势,以便材料沿坡而上,坡与塔适时等高。当建到第七级时,所垒起的土坡,已经斜斜绵延到好几里外的村庄。竣工时,再层层退土,把裹着塔身浸着汗水的泥土,通通卸下,如笋剥壳,如月出山,亮出干净的真身,在天地之间,在江波之上。
相传卜基之日,有五彩祥云,从太保山飘来,覆盖其上,神奇而祥瑞,瑞云塔,因此得名。叶向高更为之喝彩:“此殆山川之灵与千百年之气运,萃于一时,故能襄此盛举。”
历史常有得意之作,也往往留下叹息。就在瑞云塔完工前一年,叶成学不幸病逝,来不及看一眼自己心心念念的作品,常引后人感伤。我们瞻仰杰作,也是在怀念作者,怀念那些造福苍生的先贤,其功如桥,其寿如塔。
绕过一排榕树转过一弯石径,久誉“精丽甲于海内”的“南天玉柱”,赫然入眼。八角横空,檐角微翘,七层到顶,层层收分,我们离塔身太近,仰望不到塔尖,那至高处应是葫芦状塔刹。目光沿檐角顺降,只见每一个檐角都端坐一尊镇塔将军,共五十六尊。第一层朝北处,开一扇较大的门,分列一对石雕金刚护法,披坚执锐,威严雄伟。
我沿着塔座顺时针绕塔,塔座应叫“须弥座”。细看须弥座束腰处的石雕,实在精美绝伦。当初那铁石交锋的线条,晒过明朝烈日刮过清代长风,再经民国的烟雨密密洗涤,入目当知流畅,触手始觉沧桑。再读石雕内容,上枭刻满三重瓣的仰莲纹,下枭雕着波浪纹,两道饰纹之间,是成双成对的生动图腾,有双狮戏球、双马奔涛、双凤朝阳、双鹿灵芝,双兔望月等。这些独具魅力的福文化符号,千古流传,历久弥新,望云,似在浮动;看马,如有蹄声。更引我注目的是转角处,各有一位造型可爱的力士,手握海螺照天吹,吹来海风阵阵,仿佛提醒游人,举步之间,即见沧海。
我们又绕到塔的北门,沿着缝隙长草的石阶,拾级而上,塔门正上方高悬一方匾额,四字竖排行楷——凌霄玉柱。不知出自谁之手笔,叶向高?他的书法作品,我倒读得不多,印象最深的是一副对联,在福州林阳寺的梅花园里,“安知住世君非佛,想必前生我亦僧。”览其生平可知,叶相也信佛,这副对联传递出“众生皆是佛,唯我是凡夫”的崇高识见和谦卑姿态。十四个汉字,绝色如梅!
“我们登上去吧!”同行的蓝光兄身手矫健,话音还在门外,人已到塔心。我们也随即入门,第一感觉就是瞬间清凉,一石之隔,外面是酷暑,塔内已深秋。这种塔内穿心,壁内折上的设计,既方便登临,又隔热纳凉,每层的出口与入口,自成“风洞”,刚过“火焰山”的我们,自然舍不得移步,但带声的风,不停地催人向上。每层塔心中转台壁前设有佛龛,供奉释迦牟尼佛和观世音菩萨,壁上还有罗汉和飞天雕像,神态祥和,衣袂舒卷,卷成风的形状。
每跃上一层,必经塔心出口,绕过勾栏平座,再由同层入口而向上,进进出出御风而行,里里外外风华尽览。每层塔身外壁也都雕刻罗汉飞天、麒麟凤凰、天马仙鹤等图案,线条若隐若现,姿态优美传神,看得蓝光兄啧啧连声。
不久前,文博专家曾江老师送我一本他的著作《福建古塔》,书中援引德国学者艾克对瑞云塔的一段评述:“我们缘梯登塔,心中充满了明代末年的回忆,我们层层上升,渐能看见塔身外面小龛里的雕像,和尚、罗汉等等,都是近代毁像主义下的幸存者。常人对于明代雕刻之偏见,以为呆板而乏创造者,等到细看这些作品,不由得惊诧重生。”翻译这段文字的是建筑大家梁思成。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也曾到此观塔,他说:“余足迹遍海内,历观名胜古迹,浮屠之精者,无过瑞云。”丁先生有“现代徐霞客”之誉,东西方学者皆如是说,我如是信。
很快,我们登到最高层,越高则回廊越窄,栏杆越矮,若是恐高者,只好贴塔身而轻移步。脚下的石板严丝合缝,却封不住小草弱弱的身影,看样子是马唐草,有明目之功,细长的嫩叶随风,像大士手执的杨柳枝。登高正好眺远,且宜吟诗,“凭高欲远苍茫望,烟火万家荔子新。”这是明人的歌咏;“潮涌湖平龙跃浪,风吹旌动马超群。”这是清诗在接力。而我,我的目光在翻阅,翻阅龙江两岸连绵的画卷,几千楼之外是几万朵白云,哪一朵云下,是当年的太保山?母亲河在现代楼宇的丛丛簇拥中,蜿蜒东去,江海交接在我两睫交接的迷蒙地带,白鹭和轻鸥,在那里并秀温柔。小精灵作证,立塔初年,海禁已经解除,海上丝路,有丝滑的故事,也必有颠簸的情节。
风帆裹着梦去远航,家里点着灯在守望。灯代表眼睛和心灵,牵挂游子祝福远方。在历史的记忆中,塔立之后,每逢甲子中秋,必点亮层层塔灯,父老乡亲同心祈福,彼此送福,共同祝福。这温暖的习俗传承至今,距今最近的一次是1984年,岁次甲子,恰逢国庆三十五周年,当时盛况,不少福清朋友仍记忆犹新。掐指一算,下一回,再等十二年,那时,我们约好再来,再来祝福神州大地永远风调雨顺,国泰民安。那时,海上生明月,灯塔映龙江,想想,已先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