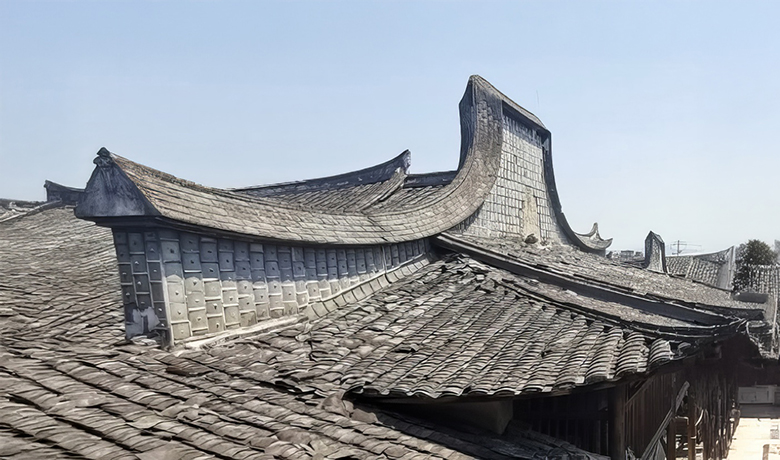郑秀杰
早春的南方,烟雨如纱,朦胧了整个世界。当我的双脚踏上福寿桥那斑驳的石板时,指尖轻触桥身,仿佛触摸到了时光的纹路,刹那间,岁月的长河在眼前缓缓流淌。这座从清代走来的古桥,历经两百多年风雨洗礼,依然静立在清溪之上,宛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,每天在咀嚼着一些淡远的故事。
有人说人生如梦。在我眼中,人生恰似一座座古桥,无论是承载着过往,还是连接着未来,都是生命旅程中坚实、可靠的依托。
福寿桥,静卧在罗源松山镇小获村山边厝自然村的小获溪上,于清道光十七年(1837)重建,是罗源现存最长的古石桥。其长达62米的桥身,从西南向东北延伸。8个船形桥墩犹如远航归来的航船,稳稳地停泊在潺潺溪流中,历经岁月冲刷,依然坚定地守护着一方水土,见证着时光的流转与时代的变迁。
福寿桥桥面由长约4米、宽约70厘米、厚近40厘米的条石构架而成,每一块条石都散发着大气磅礴与坚实可靠的气息。曾经,这里是村里最重要的官道,也是罗源通往连江马鼻古道的重要枢纽。石板上那些深刻的烙印,是岁月镌刻下的独特密码,也是无数先人在此留下的生活艰辛与美好遐想。
旧时的福寿桥,无论是烟雨缥缈的春日,还是月朗星稀的夏夜,总有人在古桥上感受着如烟似幻的水光、月华。
然而随着岁月变迁,古桥上留下了太多不可磨灭的印记。据史料记载,抗日战争时期,局势危急,当地乡民为了抵御日军的进攻,不得不忍痛割爱。他们在桥头点燃炭火,以极端方式烧断桥梁,试图阻挡侵略者的脚步。如今,站在福寿桥头,四分之一处的主体桥面仅剩下一半大小,那是新中国成立后重新修缮的断桥部分。十几年前,这里还是村民聚集议事、纳凉休闲的绝佳去处。乡民们仍清晰地记得,每当夏日夜晚,当年还是孩童的他们,常常会与同伴卷着竹席,欢快地铺在光滑清凉的桥面上,尽情享受着消暑的惬意时光。那时,严严实实的护栏环绕四周,给人满满的安全感,仿佛是一道坚固的屏障。可如今,岁月的侵蚀让福寿桥一头的护栏几乎毁损殆尽,唯有另一端桥头残留的十几米护栏,以及护栏上精美的花纹,还能让人们在恍惚间想象它往日的繁华与风采。
爱怀旧的人们,常常会以一座山、一条河、一座桥作为情感媒介,将心中无数被时光搁浅的想法与思绪,化作繁华过后的一缕烟尘。站在残破的福寿桥上,潺潺流水声萦绕耳畔。沉默不代表着无言,桀骜不羁也好,遗世孑立也罢,一座历经风雨的古桥,毕竟承载了一代人走向一代人的远方。
在罗源,还有一座令人惊叹不已的桥——位于鉴江石笏里的“坦桥”,又名“险桥”。这座桥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五年(1546),清乾隆三十三年(1768)重修。其两端以悬崖峭壁为根基,桥面横跨在宽达6米的幽深峡谷之上。原本是用三条各宽1米、厚0.5米、长8米的巨大花岗岩条石巧妙架成,如今却仅存一条。坦桥高13米,没有桥栏,远远望去,惊险万分。从前,鉴江镇的人们走陆路前往罗源县城,或是去往古田、宁德,都必须从这座桥上经过。坦桥的两头,稳稳地架在块石垒砌的石梁上。1976年修筑公路时,因岩壁上巨石滚落,将其中两条桥板砸断,如今只剩一条孤零零地横在那里,让游人望而生畏,不敢轻易通行。
关于坦桥,当地还流传一段动人的故事。清乾隆年间,在乡贡吴士魁倡议下,罗源知县马淮积极响应、大力支持,县里22名绅士齐心协力重修此桥。据说,马知县在乾隆三十二年奉旨担任罗源知县,有一次路过这座横跨悬崖的“险桥”。那时,石桥右边石梁已然倾圮,桥下湍流不息,叫人胆战心惊。马知县是在旁人搀扶下,才战战兢兢地过了桥。之后,他便将修复此桥一事记在心头。第二年,22名开明绅士出资共襄公益,马知县得知后,立即捐出半年薪俸。石桥修好后,马知县受邀撰写碑记,他深思熟虑后,将“险桥”改为“坦桥”,寓意天堑从此变成通途。同时,他还刻石勒铭,寄望这座石桥能为民众带来长久的福泽与安宁。
如今,交通日益发达,坦桥早已失去了其通行的实用功能,但桥头的修桥碑被妥善保留下来,成为珍贵文物。这块严格来说应称作“碣”的石碑,顶部呈圆弧状,碣首半圆框格内雕刻着一个张牙舞爪的黄色龙头,一根根龙须触及周围片片缭绕的祥云。仿佛下一秒,这条栩栩如生的黄龙就要腾空飞起。
站在古桥上,远处高楼林立的现代建筑与古老石桥相互映衬。我深知,古桥昔日的辉煌不再,但它们所蕴含的精神、哲理,永远不会消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