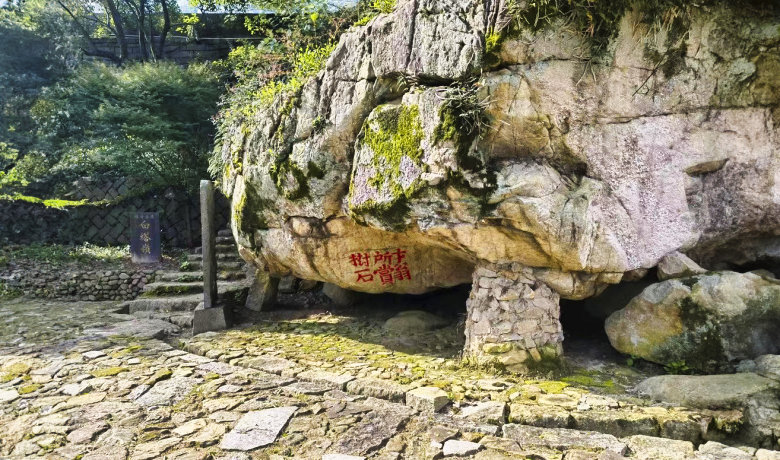邵永裕
从乡下出来的人,对老家房子,会有一种挥之不舍的感情。
自从父母过世后,很少回乡下。最近,因房子长年不住人,面临着垮塌威胁,为了让其挺直身板,面容不再憔悴,请了一些师傅,把我当年在最困厄日子起盖的房屋修葺一番,为此,我尽可能每周抽空回家看看。
房子为两层楼土木结构,1985年秋与我弟联合起盖。就在这年的秋天,我参加了工作,月薪49.5元。这些薪资除了勉强维持个人生存外,想盖一座房子,就像今天赚工资的人在一线城市买房一样困难。
通过精心估算,除了依靠兄弟添工外,要买上建房所必须的椽、瓦、桁、木料,还有一部分必付的工钱,一栋占地200平方米的六扇厝,我至少需要分摊3600多元,这还不包括初装修费用。
刚走出校园,靠微薄的工资,要想完成这么一个工程,简直是难于上青天。囊中羞涩,让我伤透了脑筋。父母供养我读了十多年书,已经费尽了心血。再也不能让一生操劳的父母再为我添盖房子操心了,我一直这么想,并努力做到。但对一个刚参加工作一个月,没有分文节余,且所需钱额又这么大,我该去哪借?
那些日子,除了工作,脑子转悠的便是这个问题。晚上,躺在床上,久无睡意。脑子不停地搜索着,哪个是朋友、哪位同学好到愿意借钱给我?同时还盘算着,朋友与同学谁有钱?经过这么一筛选,我便明确了目标,开始了筹资活动,但计划美好,往往因为实施困难而落空。那时有钱的朋友没有,同学大多刚参加工作,也都没什么积蓄,迫于感情和面子,一些同学即使表现得十二分热情,也只能借给三五十或一百元小额数目。
于是,我想到了贷款,贷大数额,没有什么可供担保的东西,难度极大。听说三五百块,可以放宽条件。可是我不认识信贷员,加上找贷款的人太多,像我这样无名之辈很难接触到。经过别人牵线搭桥,我总算认识了一个信贷员,就想贷五百元。起初他答应办理,等着他通知办手续,过了很长时间,还是没有等到他信息。彼时,贷款业务不正规,信贷员权力很大,办贷拿回扣,是公开的秘密,对于初涉江湖的我一无所知,不知是没给他送礼物,还是没请吃饭,或者小数目贷款无利可图,人生第一笔贷款以失败告终。十年后,我在城里购买商品房,因为当年的碰壁,以至于说到贷款,就心有余悸,没有选择按揭贷款,宁愿向亲戚朋友筹借。
七拼八凑,房子总算落成了。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,结婚的费用又是一笔沉甸甸的数字,用于装修房子的钱,只能集中在打家具、修洞房,以及架设楼梯等开支。房前屋后以及厅堂、沟埕的整修都无暇顾及。结婚后在这房子小住了一个礼拜。此后,便交给了父母去打理,一晃就是30年。
妻的娘家在城里,当初结婚时,就嫌我家住乡下。她住惯了城里的大宅院,始终瞧不上乡下的破房子。其实那时在乡下,我这样的房子算是不错了。虽是简陋,但门窗俱全,也刷了油漆。窗户也都上了玻璃,不像有的人家,用薄膜遮挡。盖成的房子,除了新婚之年和偶尔回家办事小住外,30年总共住不上3个月时间,基本上都住在单位。后来城里有了房子,装修的念头更是渐渐地淡漠。
就这样,父母在这装修还不完善的房子里度过了晚年。他们随着流年时光和房屋一样老去。忆想当年的无奈,父母居住的寒碜,母亲没住上我城里的房,不禁感到酸楚与内疚。
去年弟跟我商量,想在老家翻盖新房,前些日子,又改口让我一同装修土木房,我附和着,跟着凑热闹。平心而论,花钱装修乡下几乎不住的房子,还真没那必要。对于这不打紧的开支,妻子戏谑道:“闲钱补笊篱。”
但谁知我心?这座房子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件作品,也是我人生最困难时期,诞生的一尊艺术品。确切地说,我修葺的不是一座房子的概念,而是曾经残缺记忆的修补,也是弥补我早年让父母寒碜的无奈,更是整修年少时曾经为之殚精竭虑的一种心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