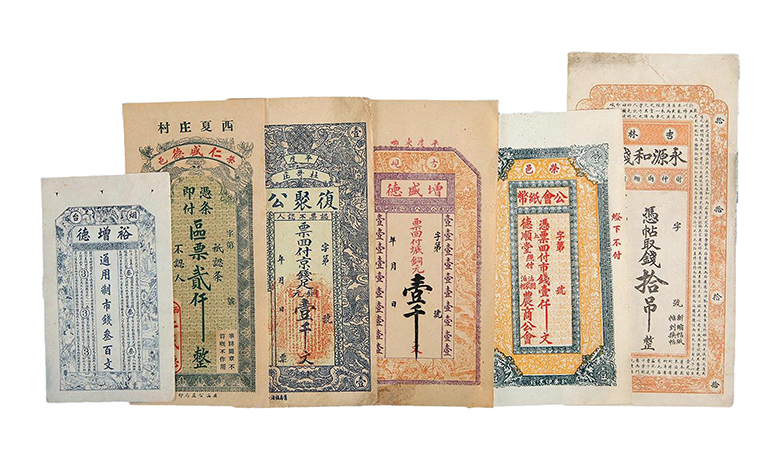宋八大家大名如雷贯耳,但以我的偏见,相对于其他七人,曾巩,也就是曾南丰先生,在今人的心目中大概是最没有存在感的。不过换个角度看,对于福州来说,他应该是八大家中最有存在感的。一来他当过福州最高行政长官知州;二来他为福州写下名垂青史的《道山亭记》。
宋神宗熙宁元年(1068)九月,程师孟任福州知州;熙宁三年(1070)六月,调任广州知州。此后福州知州更替过好几任,其中就有曾巩。元丰二年(1079),明州(今浙江宁波)知州曾巩,应已调任越州知州的程师孟之请,欣然而作《道山亭记》。
道山亭是程公在福州任内所建的,也是曾巩自己熟悉的,看来程公出了个送分题。但乌山只是弹丸之地,其亭亦无鬼斧神工可夸,怎么写呢?一切景语皆情语,景语若不能超凡,就必须倒逼情语脱俗,否则送分题就变成送命题了。
南丰先生拢了拢宽大的袍袖,撇开道山亭,视线从天而落,以文笔作画笔,工笔描绘一幅闽地行旅图。这里自周秦以来,就是交通大梗塞之所。山头相连,莽莽苍苍,中间散落几块平地,小则为县,大则为州。山路细小崎岖,爬个山坡像是在攀援粗绳子;有的路像是一丝头发垂挂在山崖之上;有的路从深险难测的溪流缝隙间蜿蜒而出,行走须防道旁尖利的石块。水从高处奔流而下,水中岩石交错,如树林若兵戈,千里不见首尾。夹缝中的水路,如蚯蚓盘结,如虫蛀刀刻,漩涡如轮,激流如矢。行船须得趁时顺势,一不留神就会船破人溺。
南丰先生缓了缓口气,笔锋一转。福州地属闽中,是闽地最大的平原,南拥闽江,东出大海。城池内外水陆通达,路旁沟渠可以直通大海,载人运货的船只日夜停泊在家门口。山上多巨木,城里多巧匠,人们最爱盖房子。城里三山鼎足而立,沿山望去,庙宇道观多达数十上百处,宏伟奇异之状,已经到了人力的极致了。
现在,该点题了。南丰先生写道,程公在掌管福州政务之余,特地在这乌山顶上修了个亭子。坐亭四顾,可饱览山水之胜景、城池之宏大、宫室之繁华。程公认为,这里地处江海之上,登临览胜,可以和道家所说的三座仙山蓬莱、方丈、灜州相媲美,所以就给亭子起名“道山亭”。
南丰先生最后升华主题:程公来此险远之地做官,巧妙利用山形地势建造亭阁,寄托耳目之娱,超脱尘俗之外,他的心志是多么高远超迈啊!不仅如此,程公治理城市也颇有建树。他“既新其城,又新其学”,市政建设与文化建设两手抓、两手硬,所以很快就调任升官了。
文似看山不喜平。一篇《道山亭记》,就是这么斗折蛇行,烘云托月。闽地险远是铺垫,衬托程公心胸之旷达;百姓安乐亦是铺垫,衬托程公治城之功绩。六七百字的篇幅,伏笔照应摇曳生姿,宛如在小小盆景上展现出伏延千里的山川气概。文学史作证,南丰先生这篇命题作文喜登优胜榜。
道山亭原始的模样,已经不可考了。《道山亭记》镌入石碑,立于亭侧。石碑初立,即为名胜,世称曾碑,直到元末仍有文献记载。后亭圮碑没,明万历年间重建道山亭,清道光年间又重建,但均与曾碑无涉。目前乌山上的八角形道山亭是1955年重建的,2008年修饰一新,并在亭北面坡下重立《道山亭记》碑。
抚摸石碑,白亮的花岗岩在春日的阳光下泛着暖意,碑文为颜体楷书,端庄、遒劲、古朴。然而,我总觉得意犹未尽。它太年轻太单薄了,难以承载近千年岁月的倾诉。
屈指算来,原版曾碑存世约三百年,读碑者想必夥矣。但最著名的读碑感慨,反倒是感慨读碑者太少了。南宋后期,词人刘克庄仕于福州,作《道山亭》诗叹道:“绝顶烟开霁色新,万家台观密如鳞。城中楚楚银袍子,来读曾碑有几人?”确实,道山之上,亭台宏伟壮丽,庙观香火旺盛,城中富贵之人流连优游,他们何必在意那篇百年前的古文呢?不过也难怪,世易时移,情随事迁,曾碑寂寞本在情理之中,克庄先生大可不必伤感惆怅。
我读曾碑,对于开篇的行路难之慨叹已经无感;对于卒章显其志的褒扬程公之词,也失去了兴趣;唯独对于刻画黎民生活场景的中间段落,玩味再三,感慨系之。
读碑而未必见碑,未读碑而未必不寓碑中意。游人三五成群,漫步而过,对身旁的曾碑视而不见。男男女女,留几声轻笑,落几句低语,风中隐隐约约飘过樱花、桃花、白玉兰的香气。这样的气息,带着朴素的快乐,与生活的本质息息相通。这样的气息,何尝不是南丰先生在宁波援笔作文揣想中的本意?
我读曾碑,在簇新的石碑前伫立良久,似乎要看穿碑后的山土。我想破解那千百年岁月的谜题,直抵那大荒之山无稽之崖,凭吊那湮灭于历史烟尘之中的曾碑。那,才是我固执地守候在心中的“真碑”。